撰文 | 张向荣
最近偶然发现,五年前译介到中国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至今仍然位居各大畅销书榜单之中。当年北大历史系高毅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言被广大读者忽视了,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很多人没有读懂这篇满纸“高级黑”的序言。
这恰恰构成一个有趣的反讽:置于一本书最前面的序言事先张扬地告诉读者,要警惕这本书内容的不可靠,但这本书却一跃成为持续多年的现象级畅销书。作者还适时撰写了《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两部作品,构成了同样畅销的“简史三部曲”。

尤瓦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译者:林俊宏;出版:中信出版集团)书封。
事实上,很少有专业人士对《人类简史》发表看法,中文世界能看到的如加拿大人类学者Christopher Robert Hallpike将《人类简史》斥之为“一部轻浮的伪史”,并驳斥了赫拉利笔下多处与人类学相关的谬误。
高毅先生并没有受到攻击,这使他的序言显得富有微言大义,毕竟,他是用“旷世罕见的历史学家”、“非同寻常的想象力”来形容赫拉利,用“不是历史”、“走向了哲学”、“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来描写这本书。如果不是读完全书,确实不容易把握这些“溢美”的真实含义。
“简史”的畅销是全球现象,绝不仅是出版和媒体营销的结果。即使有来自学术界的批判声音也无法影响其畅销。坊间更是一时间充满出版机构推出的各类“简史”,蹭热点的意图昭然若揭。所以,本文不采取学术批判的视角来看“简史”,更不敢对内容进行详细的指摘,而是聚焦其持续畅销的现象。
简史与大历史
说到“大历史”,
最先想到的已经不是黄仁宇了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历史学家。他最初研究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大历史”(Big History)理论,被认为是“大历史”教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国内已出版他的《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合著)《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等作品。
据说,赫拉利撰写“简史”系列,灵感是来自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big history)概念。这一概念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新世纪传入中国,随着“简史”的流行,“大历史”也一改沉寂局面,进入到媒体和大众视野。几年前,如果问一个普通读者何谓大历史,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准是黄仁宇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而现在已经不是了。
延伸阅读

《中国大历史》
作者: 黄仁宇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8月
所谓“大历史”,指的是一种从宇宙起源叙述到当代人类社会,包含了从宇宙到地球等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贯通叙事。在大历史中,作者就像上帝,视角从宇宙、恒星、太阳系,定睛到地球、生物圈,再聚焦到人类、农耕、现代化……直到今天。从正面意义说,“大历史”将整个宇宙作为叙述范围,从而重新定位了人类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的历史坐标。
显然,“大历史”与“简史”都具有空前庞大的历史叙述框架,其内容都涉及众多学科,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特点,但长度只是普通历史类读物的篇幅,“简史三部曲”仅仅是三本小册子;“大历史”的代表作《时间地图》只有60多万字,与“大英百科全书”之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延伸阅读

《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作者: [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
译者: 晏可佳 等
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2017年6月
于是我们发现,“简史”的“简”和“大历史”的“大”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包罗万象的意思。假如给“简史”加上具有限制范围的定语,如“中国文学简史”、“西方哲学简史”、“人工智能简史”之类,那么就是普普通通的科普书、入门书。但“人类”、“未来”两个定语并没有起到限制范围的作用,而是增强了范围广阔的语气。
同样,“大历史”的“大”也没有范围限定的意思,“大历史”是建立在如威尔斯《世界史纲》等“世界史”、“全球史”和年鉴学派基础上的,但“大”超越了世界、全球等定语,把“长时段”拉到了极致,透露着一种无限的意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简史”和“大历史”本质是同一类作品。
延伸阅读

《世界史纲: 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作者: [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
译者: 吴文藻 冰心 费孝通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5年7月
这类作品的出现,展示着人类试图消化掉现有知识的雄心壮志,也充分考虑了读者能够一次性、一口吃掉这些知识的便利性诉求。两类作品通过构建一个结构简单、结论易懂、内容丰富的框架,帮助读者用最快的时间,习得一套足以囊括所有知识的世界观,从而获得满足感和自信心。
一种“简史哲学”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今天是不可能存在的
第一次读《人类简史》和《时间地图》时,我首先会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因为,这两部书并不仅仅旨在于叙述历史,而是在人类所能知晓的全部时间内,在科学发现和人文历史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观念。
经典的历史哲学如司马迁、黑格尔、马克思等的著作,也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通古今之变”),对所选取的史料进行沉思(“究天人之际”),从而提炼出独特的观念(“成一家之言”)。在司马迁,这是由《春秋》公羊学所褒贬的世事推移;在黑格尔,这是形而上的“精神”发展和实现的历程;在马克思,这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人类永恒斗争并解放的长征。

由杨洁导演的电视剧《司马迁》(1997)画面:太史公自序。
但是,读罢“简史”和“大历史”之类的著作后,掩卷回顾,我却发现将其认为是历史哲学显然是误读。正如高毅所说,“走向了哲学,还不只是历史哲学”。高毅的意思似乎并不是称赞其达到了哲学的境地,而是嘲讽其虽然在叙述历史,但又没有尊重历史,成为了一种玄学。我觉得可以命名为“简史哲学”,以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历史哲学从来就不提供关于历史的真理,而是提供关于历史的意见。关键在于,这种意见必须是建立在对史实的全面、深刻审视之上,必须经过作者富有逻辑的沉思,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多数情况下,历史哲学还需要被置于作者整体的思想体系内来理解。所以,历史哲学学者往往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
但无论是“简史”还是“大历史”,很难发现具有这些特征。
从内容上看,两者对内容的把握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乍读“简史”,会觉得案例十分丰富,细节充盈,而且作者能对读者已经形成思维定势的史实给出新视角的解读,被粉丝誉为“刷新三观”。这是“简史”颇具可读性的重要原因。
但这是牺牲了史实的深度才做到的。一方面,这些史实的呈现并不全面,无论多复杂的议题,都只呈现粗浅和个别的一面。另一方面,作者对这类史实的评论看似独特、精彩,一扫陈腐之见,实则缺乏沉思,更多的是对专业领域的意见做“拿来主义”,且取此舍彼,因此似是而非。读者觉得耳目一新,是因为读者无从得知这些议题的全面呈现,也不了解专业领域的研究现状,当然无从判断作者的评论是否客观准确。
更有趣的是,专业人士很难通过三言两语去反驳,作者只需要几句话、拿出几个例证就敢于下一个重大结论。专业人士要想反驳,至少需要一整篇论文甚至是一本书的篇幅,拿出足够的例证才敢立论,而且语言一定会比较枯燥,读者还得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读。那么要反驳全书,还不得需要一辈子?谁会有工夫行此无聊之事呢。
“大历史”则有所不同。“大历史”无疑在深度和严谨性上更胜一筹,而且“大历史”打破学科界限的观念,的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新发展。但在实践中,为了获得立论的严谨性,作者则不得不牺牲案例的丰富性,在具体阐释每一个论题时,无法像一般历史书籍那样对事件个案、人物行为、文献材料进行详尽的分析,又做不到像“简史”那样只抛出吸引眼球的结论,所以作者只能依靠各类数据、宏观概览、简略的制度变迁来充实叙述。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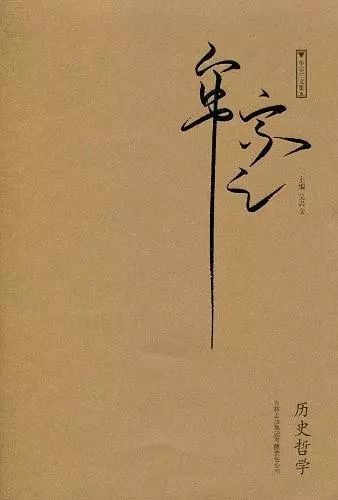
《历史哲学》
作者: 牟宗三
版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6月
在上述过程中,“简史”牺牲掉了史实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评论缺乏深度;而“大历史”牺牲掉了史实的丰富性,评论缺乏个性,因此两者均无法进行深刻的沉思,最终只能抛出一个庞大的观念,却无法阐释出一套具有启发性、原创性的历史哲学。
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今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学科的深度知识,更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处理如此庞大的内容,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今天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种做法最终只能写出“简史哲学”,无法建立历史哲学。
这种做法最终导致“简史”和“大历史”的结构虽然庞大,但很粗糙。就像一座宫殿,远看高大气派、金碧辉煌,近观则发现是泥墙茅檐,一下雨到处漏水。有人指责“简史”就是公共号文章,这固然有失偏颇,但也似乎捕捉到了那么一点神似。
也有人辩护说,这两类作品都是入门书、科普书,不应以学术标准衡量。但是,科普书和入门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指南针、路标牌、导航系统,是给读者打基础,并不是给读者传播一套高高在上的世界观。“简史”和“大历史”从性质上说均不属于科普和入门书,事实上,两者的畅销也不是因为其具有科普性和入门性。
畅销的秘密
大多数读者,
是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
“简史”和“大历史”畅销的秘密,根本在于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简便易懂的世界观。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信息已经爆炸,每天都有新的知识被发现,认知的边界以加速度拓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需要阅读、理解、梳理、容纳大量知识,并结合漫长的自身实践,才能逐渐形成对世界的整体性看法。但如今,大多数人很难有这样丰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他们虽然感觉到了知识在快速更新,感受到了自己世界观的日渐窘迫,但难以好整以暇地沉思自己的观念。
“简史”和“大历史”把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装入一个极简且极具普适性的叙述框架里,从而“毕其功于一役”,帮助读者迅速建立一套完整的、成体系的自然观、历史观、世界观,把读者碎片化的新旧知识整合起来,给旧的世界观打上补丁,升级知识系统,甚至全部替换。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读者在读后感到“刷新三观”,感到很充实的原因
众所周知,一套理论越是包罗万象,越是显得“放之四海而皆准”,反而越不可靠。但是,渴望尽早获取新知识以预测未来商机的商界精英、害怕知识落伍被时代抛弃的白领、好为人师夸夸其谈的“交际草”(主要是男性)以及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期的学生,在接纳这一世界观后,其新旧知识就能在一个简单的框架内各安其位。从此,他们对人世间所有的事都能说上两句,获得一种“感觉自己很博学”、“对整个宇宙的看法从此清晰了”、“仿佛自己成了建立体系的哲学家”等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在中国,这类读者多数是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对知识是尊重的,对生活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恰恰是因为此,才使得这类人能够敏感地意识到世界的高速变化,接受自己无力无暇进行专业学习的现实,感受到对未来和阶层下坠的不确定。对知识的信任会带来缺乏知识的焦虑。那么,一套能够整合新旧知识的世界观,即使漏洞百出,也远比提供一种专业技能、一个具体知识更受欢迎。
一本书,当然不应因为畅销而受到指摘。
我们至今还常常使用“命运”这个词,是因为人生原本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简史”和“大历史”能够用一个粗糙但稳定的世界观,消除(尽管也参与了焦虑感的制造)许多人的焦虑感。
知识核爆炸的时代不允许也不需要每个人都掌握何等丰富的知识,或拥有怎样高深莫测旷世绝伦的世界观。对大多数人来说,“简史”和“大历史”的世界观已经够用了,而对那些拥有好奇心、热爱沉思的人来说,这样的世界观也框不住他们,他们会从“简史”和“大历史”对知识边界的拓展中,获得新的启发和兴趣点,从而超越这一世界观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