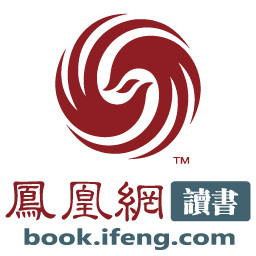正文
现在我还爱吃瓜子,常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外面摊子上买,挺邪门的。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只要有电影就去看,一部电影即使看过两遍三遍也还要去。父亲是教语文的,每次都会布置一个任务,让我看完这部电影回去再复述一下故事。真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上电影学院还要学这个,写故事梗概,我小时候就写过这个嘛。父亲的培训让我对电影和文字有了一定的敏锐度。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电影,但是电影院的票已经卖完了。父亲认识电影院的人,就把我带到电影院的放映室,在楼上放电影的
孔那儿看完了电影。我跟其它小朋友不太一样,小朋友每次看电影都会特别当真,“啊,那个演员肯定死了,那个人被坏人打死了,演坏人一点都不好,就会倒在那被子弹打死,英雄也会被打死。”他们会觉得那个人真死了,吵半天。
我也会被故事吸引,为英雄牺牲与敌人的死感到惊恐。但一看,电影是用机器投影到屏幕上的,装的是胶片拷贝。我知道这是假的,虚构的东西我从不会去当真。但我也愿意投入到剧情很真的感情当中,所以我从小就知道那是虚构编制出来的东西,也喜欢去看。
走自己的路
中学之后我变得十分叛逆,
1982
年我上初三,有一次母亲偷看了我的日记,姨妈说
:
“你妈为什么不能看你日记?”我站在床上暴跳如雷,“你们看我的日记是在侵犯我的人权。”我不知道谁教我的,没有任何人。县里面选举,爸爸妈妈去投票,回来我就质疑他们,母亲讲领导画好圈他们说投谁就投谁。我说这是不对的,选举应该你信任谁才选谁,我觉得这些质疑或者说怀疑精神融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我愿意相信最爱我的外婆告诉我,我们村那个地主是好人,而不愿意相信课本上描述的地主有多可怕有多坏。我不相信老师,不相信《**日报》,不相信课本,选择相信我的外婆,相信一个人说的话。我很庆幸亲人能够教给我人性的课程,让我在那么早没有被洗脑。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写作者。
上高中后我桌子上摆的都是语文和小说,数理化从不看,几乎一到晚自习就逃课去看电影。坐在教室里往窗户上看老师有没有在外面,“蹭”的一下就跑了。我当年写的日记现在还记得,第二天被班主任训话,“你昨天晚上去哪了,带着班上的女同学去电影院看电影?”老师就以为我跟女同学有什么事,根本不知道我是喜欢男生的。
爸爸妈妈给我买豆浆油条的钱,过年的压岁钱,我都省下来看电影,不吃就饿着。那时哥哥也喜欢文学,他就把所有的钱省下来去买《三国》的小人书。但他没有我幸运,他是按照妈妈的要求去读书、去考大学,
16
岁就考上大学。
1983
年,我在《大众电影》杂志上发表人生的第一部影评《充满希望的一年》,把当时全国那些电影厂上一年生产的所有电影做了一个点评,那一年我念高一。同年在《中学生》杂志上也发表了文章,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碰巧当时刘晓庆发表了自传《我的路》,看到后我更加坚定要走自己的路,成为一个作家。
1985
年,我非常渴望离开家乡云阳。有一天在学校橱窗上,看到《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启示,便汇款过去买了招生简章。后来听当地的人说,这里从没有人有过这么大胆,敢独自去报考电影学院。我看了招生简章后发现北京太远,碰巧武汉也有考点,便从云阳坐船到宜昌,再从宜昌导汽车到武汉去了。
我是家里的反面教材,父母不同意去,我就偷偷翻开母亲的被子,偷了她们的钱当路费,但不够。
1983
年我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文,当时的稿费是二十几块钱。河北滦平县叫王兆梅的一个女孩给我写信,她是一个农村人,已经中学毕业了,在做花卉养殖业,希望我能够支持她的事业。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也不管她是否是骗子,便把钱寄给了女孩。但是没想到王兆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