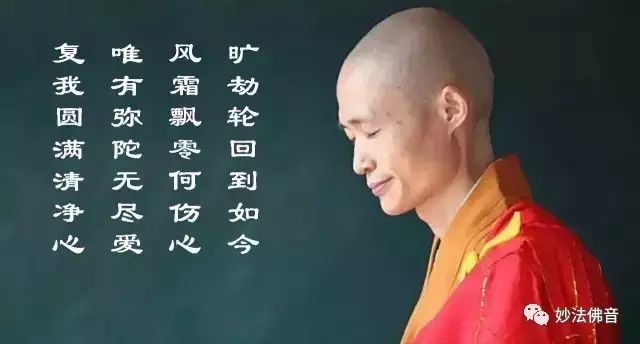正文
第三证,十万大山以南,循丈二河两岸,南抵新安州,滨临大海,皆为中国界;
第五证,思兴水西岸潭下、河桧、六虎村一带,为中国界;
第十证,海面快子笼、青梅头以南,至九头山附近诸岛,皆为中国界。
各条下皆附有证据,按张之洞说法,“综此十证,确为中国老界无疑……图籍案卷炳然可稽,则辨认尤不容含混者也”。所谓“确证”者,多系书证,且注明出处,以示皆有所本——
大抵该处中国老界确凿可据之证共有十端,皆系原本本朝史馆官书、部案公牍刊本、省府县志、知州学官册档、印契、越南国王印文、峒长世传有印分单,正与前奉谕旨以《会典》《通志》为主之意相符,实应全行辨明认还,方昭公允,与滇、桂边地新与法人商议改正者迥然不同。
此处“参稽志乘,调查档案”,正许同莘所谓“以考据施于交涉者”。综括言之,张之洞据以“证成”其说所参“志乘”“档案”,大致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史书、图经、《大清一统志》、各省、府、州志(以《廉州府志》之“记事门”“经政门”“建置乡都门”“艺文门”、《钦州志》之“古迹门”为主)、《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东华续录》(王先谦)、《钦州学册》《钦州州判档案》、明万历、嘉靖年间峒长分单、清同治十年越南国王呈覆、光绪十一年五峒绅耆廪贡生禀文等。
 《大清一统志》书影
《大清一统志》书影
 (嘉靖)《钦州志》书影
(嘉靖)《钦州志》书影
张之洞确似具有某种“函雅故,通古今”的素养,能以历史考据的方式,运用于手腕之下。他对北洋大臣李鸿章表示:
汉唐铜柱,宋元志乘、前明印单、本朝学籍,可为旧界确据。
同一书也,考据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考据之材料。此处大有触类而长、触处成圆、天下载籍皆为我所用之态。“详列旧界确证十条具折入奏”,清晰显露了张之洞作为“学问家”的底蕴,及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的取向。这也许即其著名的“书生习气”之一面。
惟说古道今,有难易二途。方志名家章学诚尝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
(《文史通义·外篇三·修志十议》)
。本朝本事,随近逐便,可据者伙,至于古早时代,去今愈远,则愈难言之,如“汉唐铜柱,可为旧界确据”“分茅岭属古森峒,为汉唐立铜柱之所”,皆论之凿凿,然依附前修,信古最深,难免据守之病,借古喻今、古为今用, 又易过度引申。许同莘说“文襄博考载籍,参以志书档案,以为沿边之十万大山,为马伏波立铜柱处,今铜柱虽已无存,而此山必应属于中国,以复汉界之旧”
(《公牍学史》,227页)
,便是一个显例。事实究竟如何,值得仔细分说。
所谓“马援铜柱”,指东汉光武帝统治时期,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爆发征侧、征贰姐妹领导的“二征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率军平定征氏起义,传说胜利后在其所至之地树立“铜柱”,以作汉朝最南方的边界。今存关于东汉时代的史籍如诸家《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记》中均无“铜柱”的明确记载。唐代人李贤注《后汉书·马援传》,引晋人顾微《广州记》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实际上,《广州记》的撰者是晋代人,其时代上距后汉初已经二百多年了。另有学者指出,“最早的记载见于《初学记》引张勃《吴录》”
(胡鸿《溪州铜柱是怎样造成的》,《文汇报·文汇学人》2018年3月30日)
。按张勃为孙吴至西晋时人,其书成于吴亡之后,此时距离马援征交趾,亦已经过去了约两百四十年,相当于今天到乾隆中期的距离。然后世多以“马援铜柱”“马柱”为典实,视如南疆界限标志,史不绝书,历代骚人墨客更对这一“历史古迹”情有独钟,题咏相续。近世学者陈登原尝抄撮相关记载,汇置一处,按语谓“马援铜柱故事,自晋到清,传说亦绵延不绝”
(《国史旧闻》第一册(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72-373页)
。
马援在西南边陲地区立铜柱,表汉疆所及,至明清时代,为之立祠立庙,教化粤民,铜柱分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似渐为汉夷之共识。明代广西参政蒋山卿撰横县《伏波庙碑记》,述马援远征伟迹,“驱逐交蛮,还之故地,界岭分茅,标题铜柱,以限南北,此则识度超迈,处置得宜,筹算计略,已岿然为末世之规矣,是之谓智”;清嘉庆官修《广西通志》有题赞曰“千百年来,交人顾视铜柱,信如蓍龟,终不敢踰跬步,以争尺寸之地”。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奉命总督两广,平定思恩、田州土酋叛乱,发现祭祀马援的伏波庙遍布粤地,民众为之顶礼膜拜,有诗咏“马援铜柱”事——“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诗尚不磨。”
(《梦中绝句》)
至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西巡抚马丕瑶奏曰:
广西地极南徼,土汉杂居,自秦汉以来,达人杰士垂勋布惠者,代不乏人。而能千百年后,村野之丁男妇孺、土属之椎髻猺獞,无不感慕讴思,旷代如新,争出其纤啬力作之资,私为创造祠庙书院,则惟汉臣伏波将军马援、明臣两广总督王守仁为最著。臣校阅所经,南宁府城及所属多有马援、王守仁祠庙。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〇二,光绪十七年辛卯二月)
马援铜柱鲜有人亲目所历,亦未见可信服的史料证据,真相已莫可究诘;至于铜柱到底立在何处,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埏《马援安宁立铜柱辩》)
;而流传的铜柱铭文有多个版本,诸如“铜柱折、交趾灭”这样朗朗上口的警策文字
(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
,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何以一个似有若无的铜柱能激起后世持续的反响,文人学士为之记载、题咏、考证,层出不穷,官方为之宣传、模仿、推广,不遗余力?或在于铜柱的政治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其本身存在价值。唐、五代借鉴史书记载中的马援立铜柱史实,征服少数民族后在当地树立铜柱,马援成为马氏竞相攀附的“英雄祖先”,如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湘西永顺县芙蓉镇溪州铜柱,兼具纪念碑性和实际政治功能,可视作一个典型
(胡鸿《溪州铜柱是怎样造成的》)
。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兼具纪念碑性和实际政治功能的溪州铜柱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兼具纪念碑性和实际政治功能的溪州铜柱
 传说中的马援铜柱铭文
传说中的马援铜柱铭文
关于马援铜柱的“传说”常常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互相矛盾,然乐此不疲者大有功夫在诗外之妙。陈登原说,“铜柱传说之外,尚有戍卒遗留之传,此一事也;援尝征武陵蛮,近世尚有土司自称援后,此二事也;至曰郡县其地,盖已有改土归流之预影,则三事矣。灌输文化,至于祠祀,则四事矣”。当政者其实不太会关心铜柱存在的真实性,而乐于利用史实乃至传说佐证现实,借史书赋予马援的褒扬美化自己,推广铜柱成为中央王朝在西南边地“改土归流”“灌输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这种管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清人乔莱《游伏波岩记》记:“粤人祀伏波,如蜀人祀诸葛。”近代历史学家、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以后视眼光赞道:“伏波铜柱,照耀千秋,宜哉!”在历代君王、官僚、士绅的合力提携和利用下,“马援铜柱”附会成形,成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征服和统治的“铁证”,也渐演变为疆土统一的一种象征
(王元林、吴力勇《马援铜柱与国家象征意义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
至晚清中越会勘边界之际,张之洞上《钦越边界亟应改正折》,认为“三不要地”原属中华,后为越南侵占,现归法人保护,应在勘界时收回,其重要“凭据”之一即为“铜柱”——
最高之山曰分茅岭,岭有铜柱,实为历朝中华边徼之地,
远凭铜柱,近据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