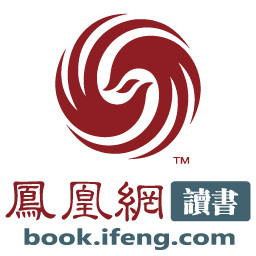正文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反、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明显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做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 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一九七八年在友谊宾馆社科院租用的工作室里,沈从文和王序(中)、王亚蓉(右)一起探讨在编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所碰到的问题。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1964 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唯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做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1953 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