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羲之虽然出身琅琊王氏,但却属于家族内较弱的一枝,幼年失父的变故,更使得王羲之经历了艰难的少年时代,产生了与家族的隔阂。
王羲之因幼遭凶变,性格老成持重,且不务清谈,有实干之才。王敦、王导等王氏宗族领袖对这个优秀的侄子都很看重。王敦曾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即阮裕,时为王敦大将军府主簿,素有盛名。王敦将少年王羲之与阮裕相提并论,大有为王羲之延揽美名之意。王导曾写信给王羲之,谈到家族内人才凋零,说:“虎豚(王彭之)、虎犊(王彪之),还其所如。”意思是王彭之、王彪之就像他们的小名一样,如同猪牛,言外之意是称赞王羲之,希望王羲之发挥才能,为维护家族利益做出贡献。
然而,王羲之对其伯叔辈的关照并不买账。王羲之曾自称
“素无廊庙志”,
又曾致书殷浩说:“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王导曾多次安排王羲之出仕,但都被王羲之拒绝,甚至发誓决不当官,使王导不得不放弃。
王羲之一再拒绝王导的好意安排,这体现出王羲之和王导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王羲之与王导的关系为何不正常?
我有一推测:王羲之之父王旷兵败之后,并没有死,而是在刘渊手下或为囚虏,或为降臣,此时,王羲之当然希望朝廷早日北伐,击破匈奴,才有可能救出父亲,但是,王导等人考虑的首先是巩固其在江东的偏安地位,所以口头上号称“恢复神州”,而实际上无意北伐,因此,于公于私,于国于家,王羲之都对王导的政策很不满意。王导大概也觉得自己的政策对王羲之父子来说不太公平,因而积极推举王羲之当官,以弥补亏欠。可惜,王羲之不买这个账,拒绝了王导的示好,直到他找到了郗鉴这个新靠山,才开始步入仕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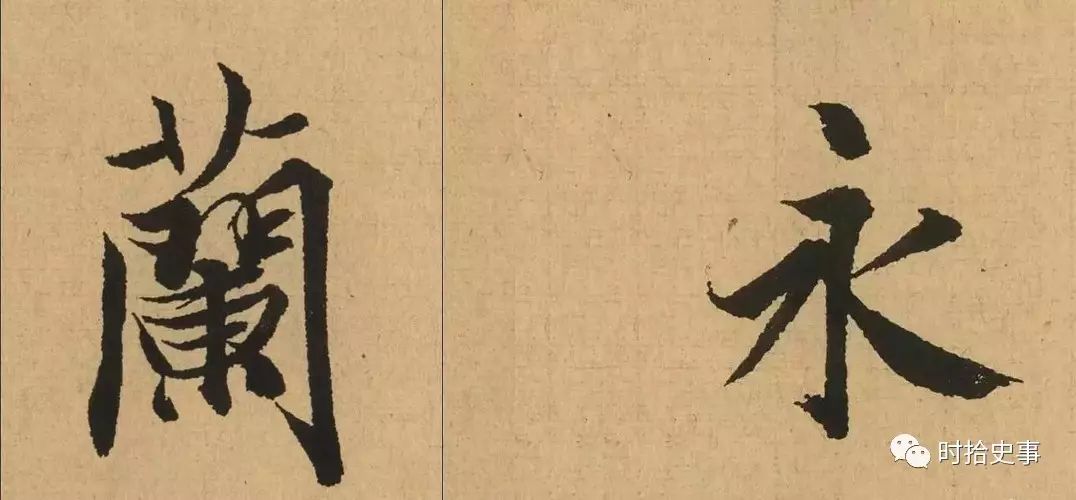
郗鉴出自儒学世家高平郗氏,其曾祖父郗虑是汉献帝时御史大夫。永嘉之乱时,郗鉴率宗族乡民千余家数万之众保据峄山(今山东济宁),司马睿署其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年),郗鉴退守合肥,入朝为尚书令,但仍控制着江北的流民大军。王敦之乱,郗鉴引刘遐、苏峻等流民势力入卫建康,对平乱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敦死后,琅琊王氏专掌重兵的局面被改变,王氏势力开始衰落。此时,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相互对立,争夺朝廷和地方藩镇的主导权,而高平郗氏则周旋两家之间,三角关系十分微妙。
郗氏既处折冲之地,遂成为王氏和庾氏都想拉拢的对象。因此,王导辟郗鉴之子郗昙为司徒掾;郗鉴要选女婿,王导说:“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最终,郗鉴选中的是在东床坦腹而食的王羲之。郗、王联姻,是足以影响当时政局的大事,更是两家的大事,王羲之却于选婿之际依旧放浪形骸,显然不以家族大事为念。然而,郗鉴看中的正是这种独立的性格和其特殊的家族地位,王羲之可谓歪打正着,拥有了家族之外的政治靠山。
在郗鉴的推举下,王羲之起家出任第一个官职秘书郎。秘书郎隶属秘书省,秘书省是中书省的分支机构,负责呈递尚书奏事、管理文书图籍、编撰国史等事务。秘书郎在秘书省内部属较低层级办事人员,品级不高,但职责重大,经常有机会接触皇帝、宰相等权力中心,是高级士族子弟进入仕途的常选。王羲之出任秘书郎的时间是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时年23岁。作为琅琊王氏族中出类拔萃的“佳子弟”,23岁才进入仕途算是很晚的了。
王羲之在秘书省工作了三年时间,于咸和三年(328年)调入会稽王府,任会稽王友。咸和三年正值苏峻之乱,王羲之却能离开岗位,可见他在秘书省并未担负特别重要的职责。“友”是王府的高级官员(《晋书·职官志》载:“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甚高,相当于王府的三师三公,一般多以才学出众、品行高洁、声望卓著的人物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