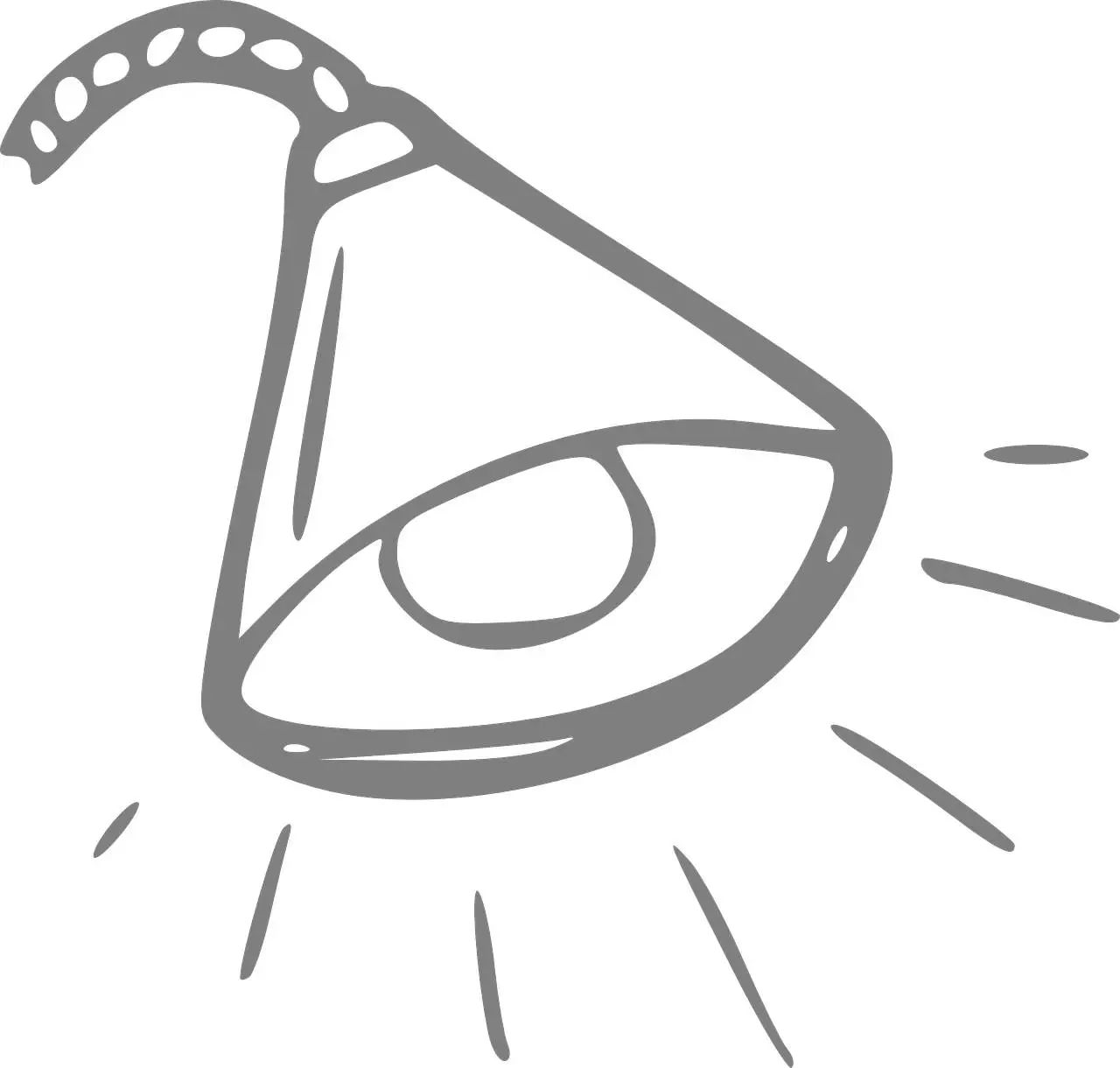正文
现在引发过敏的树木,过去曾经是城市绿化的主力。根据北京市园林局的说法,北京周围分布的风媒植物主要是杨柳和松柏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
的造林绿化树种,也是北京园林绿化的骨干树种
[4]
。
过去十几年里,北京也开展了两轮百万亩大造林工程。对于缺少绿色的北方,这样的大规模造林确实有必要,2012年以前,即使把行道树、防风林带以及房前屋后的散生树木全算上,平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也才14.85%
[5]
。
考虑到能活能绿、长得快的要求,树种上就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优先去种杨树。需要冬季的绿色景观的时候,也只能去种松树和柏树。
“过去造林这个过程留下来的树种,可能还会在非常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顾垒说。
杨柳、松柏等树种的广泛种植,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绿化率的要求。顾垒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适合北京气候条件的树种选择本就有限。
“在北京,能够成荫的树选择真的不多。”顾垒在欧洲时,发现当地会用椴树作为绿化树种,不仅美观而且属于蜜源植物。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种类的椴树,但在绿化树种缺乏多样性的北方,椴树却没有成为城市绿化的主要选择。
“北京不种椴树是因为夏天太热太干,这些树在这里受不了。很多潜在有价值的树种都因为本地的气候原因得不到大力推广,若要种植,需要额外花费大量成本去照料,在这方面投入的社会资源可能比去治疗花粉过敏要多得多。”顾垒说。
实际上,绿化树种遮荫、造景的需求,而且需要生长速度足够快,这本身就限制了树种的选择。即使自然条件相对适宜的欧洲,为了满足这些条件,政府也大量选择致敏的法国梧桐
(悬铃木科)
作为城市绿化的主力植物
[6]
。
除了树种的选择,花粉爆表的另一个因素经常被忽视,那就是树木的性别。花粉过敏之所以如此普遍和严重,一方面是因为产生致敏花粉的树种在城市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则在于城市绿化中广泛种植的往往是雄性树木,而正是这些雄性树种产生了大部分的花粉。
宗桦表示,致敏花粉来自雄性植物,但城市绿化之中为了防止落花落果、方便管理,同时考虑到一些树种雄性的姿态更好,很长一段时间里优先选择雄性植物成了园林绿化领域的共识,忽略了雄性树种的过敏问题。
树木性别的选择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顾垒认为,相比雄树花粉过敏,过去大家其实更关注雌性树种飘絮的问题,飘絮不仅惹人厌烦,还有火灾的隐患。而且雄性树木没有果实,像银杏这样果实腐烂非常难闻的树种,大家都倾向于种植雄树。
近年来,由于花粉浓度高于以往,出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绿化树种繁殖的暴发期。但在顾垒看来,这样的花粉浓度只能说是以后的常态。顾垒表示,“这不能称为暴发期,只能说这些树长大了,以后每年都会这样。侧柏可是能活两三千岁。”
“绿化这方面的规划,它产生的效应可能是以百年计的。种下一批树,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如果想要彻底清除替换这批树,可能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顾垒说。
打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到许多过敏患者在这方面的迫切呼吁。“应该马上停止种植柏树,将原来的柏树砍光”“能不能申请给树做个绝育或者把树挪走?”“那么多种类就不能选别的安全树种吗?”
2015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也提到自己饱受花粉症困扰,并想出对策:砍掉全国的杉树,代之以其他树种。
不过,砍树真的能缓解过敏问题吗?顾垒不赞成,“以这些树产生花粉的量,哪怕砍掉一半,可能产生的效应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早就过饱和了。”
砍树之外,其他缓解花粉过敏的手段,现在其实已经在实行了。
2021年,针对花粉过敏问题,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对花粉过敏源植物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建成区使用刺柏属
(含圆柏属)
、蒿属类、豚草、葎草等易致敏植物;对于花粉飘散情况严重的,通过修剪花枝、人工洒水喷淋增湿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花粉在空气中的飘散;对于距离建筑外窗立面过近,为群众生活带来困扰,且无法通过修剪等方式减少花粉飘散的过敏源植物,应更换为适宜树种
[7]
。
这些方法更适合用在人群密集的重点地区,以缓解花粉症的严重程度。要想把这些措施拓展到整个城市,那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重重困难。要么效果有限,要么代价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