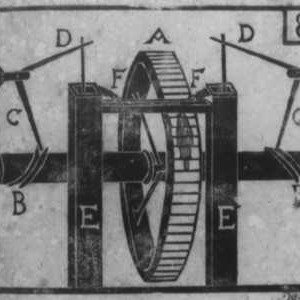正文
)一书中,他深入挖掘了这些表面可见却依旧神秘的群体。
梅休估计,
伦敦约有1000名
猫肉贩
,服务约30万只猫,平均每户一只
(考虑到一些家庭养多只猫,还有不少流浪猫)
。
这个数字看似利润丰厚,但当梅休向这些商贩询问细节时,得到的却是辛苦谋生的故事。一位
猫肉贩
告诉他,他每天步行不少于30英里,甚至经常超过40英里。
伦敦
伯蒙德赛(Bermondsey)猫肉贩的明信片,1918年。©
wikimedia
最好的销售地段是商人、技工和劳工的居住区,而那些广场后方马厩里的马车夫是特别好的顾客。“‘那里生意更密集,’我的线人说道,‘老处女是最差的,尽管她们数量众多。她们拼命压价,让我们几乎无利可图。她们付半个便士,再欠半个便士,
过一两天就把这茬给忘了。’”正如往常一样,
“猫老太太”成了危害资本主义及其服务者的罪魁祸首。
这幅铜版画,描绘了一位妇女在伦敦贝特莱姆医院外给猫狗提供肉食的场景,出自理查德·菲利普斯(
Richard Phillips)的《现代伦敦》
(Modern London),1804年。©
wikimedia
接下来的20年里,随着媒体对
猫肉贩的报道越来越多,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虽然他们大多数还算体面,但在社会地位上属于较低阶层。有些人是“生来就从事这一行”,但也有些是在原有职业生涯的尽头才转入这一行的。
两种常见的情况是:一是开业失败、失去店铺的屠夫;二是因长期吸入有毒油漆而身体垮掉的马车漆匠。到了19世纪末,看到女性
(通常是寡妇)
负责一个售卖路线的情景也不足为奇。有些人用旧婴儿车来装肉卖肉。
“伦敦生活场景——猫肉贩”,插图来自1880年11月弗兰克·莱斯利(
Frank Leslie)的《大众月刊》(
Popular Monthly)。©
wikimedia
“猫肉贩被狗袭击”,插图来自1876年8月26日的《警察新闻画报》(T
he Illustrated Police News)。©
wikimedia
那些能远离酒馆的
猫肉贩,
有相当机会积攒一小笔盈余,从而过上稳定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是主日学老师。
行业内有一套严格的规则,规定谁“拥有某段路线”,若有人试图强行插足,后果自负。盈利丰厚的售卖路线甚至会通过在本地报纸上刊登小广告的方式转手出售。
行业的职业风险包括被饥饿的流浪狗伏击,或者在推车不慎翻倒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库存被一群毫无付款打算的猫主子大快朵颐。
这种噩梦般的情境——家猫瞬间化身成一群贪婪的猛兽——令人不寒而栗,也让人联想到与猫食生意相关的一系列恐怖传闻。
最关键的问题是:猫肉贩售卖的是猫肉,还是卖给猫的肉?
这种模棱两可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夜不能寐,担心流浪猫,甚至是家中宠物猫,会被做成兰开夏炖菜端上餐桌。理智的父母和保姆尽力安抚孩子们的不安,但他们自己心里也在琢磨近期报纸上的新闻——确实有猫最终被端上人类的餐桌。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1871年,而就在同一年,英国最受宠爱的猫咪们正兴高采烈地在第一届水晶宫猫展上亮相。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由于普法战争最后几个月德国军队对巴黎的围困,食物供应陷入危机。
为了寻找新的蛋白质来源,走投无路的巴黎厨师开始经常在菜单上添加猫肉、狗肉和鼠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