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法案到底是剥离还是封禁?
TikTok“不卖就禁”法案在字面上并未使用封禁这两个字,而是规定如果TikTok不能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完成剥离出售,任何美国公司都不能继续为TikTok在美国的运营提供服务。
美国国会正是为了规避直接封禁媒体平台的法律风险,而采取了迂回的立法手段。这显然是能够打消一些大法官的顾虑的。
Alito大法官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美国长期以来就有限制外国主体运营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统,限制媒体所有权不代表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Barrett大法官说,TikTok不一定要关门,只要1月19日之前完成出售就行。Jackson大法官说,看起来本案的实质和言论自由无关,而是关于TikTok能否和字节跳动继续合作,特别是国会能不能立法禁止美国公司和敌对国家和外国对手合作。Roberts大法官说,国会对言论表达没有意见,他们有意见的是他们认为正在收集美国个人信息的外国对手。
TikTok律师只能反复强调因为全球共享算法等技术原因,TikTok无法实现与字节跳动的剥离。不知道大法官们能不能听得进去。
TikTok律师还提到,法案规定的270天的出售期限实在太短,根本不可能完成出售。
Gorsuch大法官则是直截了当地问,按照你的逻辑,不要说270天,是不是不论给多少天都没办法完成出售?
TikTok律师只能硬着头皮回答,是的,不论给多少时间,出售都是极度困难的。
Kagan大法官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她虽然承认法案可能会使得TikTok关停,但这些后果可能都是附带性的(incidental)。
附带性影响是第一修正案里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大意是说,虽然某些政府行为会对言论产生限制效果,但这些限制不是政府行为的主要目的,只是附带产生的。因此即便有这些限制效果,仍然不认为这样的政府行为违宪。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认定TikTok关停是法案的附带性影响,判定法案合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Roberts大法官的提问比较中性,他只是问,对公司所有权的限制是否等于对言论自由的管控,过去有先例吗?
TikTok律师回复,波及面和影响像TikTok案这么大的,确实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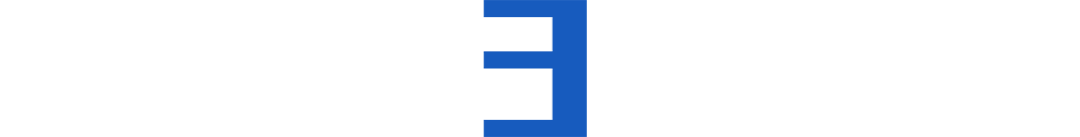
算法黑箱和隐形舆论操控
本次庭审最重要的关键词是隐形舆论操控(covert content manipulation)。美国政府律师指称TikTok通过推荐算法,以难以察觉的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美国大众的认知。
这也是本案美国政府律师的一大法律发明。在第一修正案的规则下,如果美国政府仅仅因为言论内容(哪怕这些内容是亲中反美的)而对言论平台采取措施,这些措施都很难通过第一修正案的审核。
美国政府律师找到的论述方式是,他们打击TikTok,不是因为平台内容亲中反美,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操控平台的方式是隐秘的,无法实施有效监管。他们打击的是方式,而不是内容。
如我们所预期,Barrett大法官对这个观点很感兴趣。她再次提及她在NetChoice案中的意见。她这次更为明确地说,美国人的确有权发表亲中反美的言论,但本案中TikTok受保护的言论行为其实是它的算法和编辑推荐行为。美国政府没有限制TikTok使用何种算法,他们只是禁止中国政府通过TikTok对美国实施隐形舆论操控,这是TikTok和诸多其他案例的不同。
TikTok律师只能否认三连,我们没有任何隐形舆论操控的行为,TikTok在美国的内容也是由TikTok美国公司独立运营的,TikTok只是需要使用来自字节跳动的算法,但具体执行是由美国公司独立进行的。
Jackson大法官也明确提出,“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对手操控这个平台上的内容”和“美国政府厌恶平台上内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值得关注的是,Kagan大法官有相当有利于TikTok的表述。Kagan大法官说,美国政府认为TikTok的国家安全威胁在于中国政府可能借此搞隐形舆论操控,现在这么一闹,所有人都知道TikTok有中国背景,那还有什么隐形操控可言呢?
美国政府律师说,中国可以通过算法来操控舆论,而算法是不透明的,美国公众也无法知道算法背后的逻辑。
Kagan大法官马上抓住了美国政府律师的漏洞。她说,所有社交媒体的算法都是黑箱,不能仅仅因为有算法,就说它是隐形舆论操控。Kagan大法官还提到冷战时期的例子。即便是在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没有要求美国境内的组织全部切断和苏联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