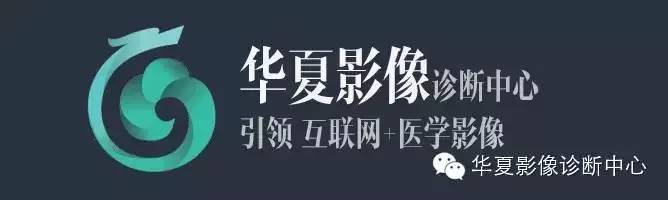正文
更有甚者,它们都直接展现了对女性的暴力和扭曲的性爱,这都对审查制度和评论家们提出了相似的挑战。但是,《偷窥狂》和《眩晕》之间的相似性虽然没有前者同《精神病患者》看上去那么明显,却更为强烈。

《眩晕》
当希区柯克想要缓和评论界对《精神病患者》的恶评如潮时,他声称,无论影片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有多邪恶,这部作品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娱乐片;鲍威尔从来没这么说过他的《偷窥狂》,而希区柯克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眩晕》的严肃性。
它们都是极度浪漫主义的作品,都以爱情与死亡的纠缠爆发为剧终,这让那个活下来的人(安娜·马西[Anna Massey]、詹姆斯·斯图尔特)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观众身心俱焚、无所依靠。
随着岁月流逝,评论界对这两部电影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精神病患者》上,但其戏剧性仍然不及《眩晕》和《偷窥狂》;想当年,它们都是被人嘲笑或指责的失败之作,但现在,它们无论是在学术界的电影研究中,还是在批评性的文字中,都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眩晕》
它们拍摄于一个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它们走在时代的前列,而属于它们的时代也终于到来了。
它们不是那种希图迎合在1950年代晚期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建制的电影,这个建制长期以来都在鼓吹现实主义的常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信任商业和幻想。
在《视与听》1960年秋季刊中,理查德·劳德(Richard Roud)提到了电影批评在法国的兴盛,这篇文章用一张《眩晕》剧照占据了一整页。劳德说,在法国,《眩晕》被评为该年度最佳电影之一,而它另外的选择更加令人吃惊——那是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和萨姆·富勒(Sam Fuller)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克洛德·夏布罗尔(Claude Chabrol)和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还刚刚出了一本关于希区柯克的书,他们在书中说希区柯克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形式发明者之一”。

希区柯克
劳德说:当人们看到这些报道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或许是认为这些人都是傻瓜”,但他也接着提醒,这两位作者参加了新浪潮运动,他们在运动早期所拍的那些电影看上去并不傻。
这起争论事件的结果是勒琼离开了《观察者》,不再担任该刊的电影评论家,从30年后的眼光看来,她的离职只不过是电影文化巨变的一个侧面,在彼时,这种变化已经无法被遏制了,而对希区柯克——以及日后对鲍威尔——的日益提升的重估,是这一变化的中心事件,也是它的表征性事件。

《偷窥狂》
在《偷窥狂》和《眩晕》的叙事正式开始之前,影片中都出现了巨大的眼睛特写,这仿佛是想在第一时刻引入视觉与主观性的主题。在《偷窥狂》中,我们看到的是闭合的眼睑,我们发现眼睑之下眼珠的快速运动,表示这个眼睛的拥有者在做梦;然后,这只眼睛大大地睁开了,我们由此进入故事,一个具有梦幻般或者说噩梦般浓缩逻辑的故事。
当《眩晕》的片头字幕出现时,镜头则在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的脸部运动。它先是对准了嘴巴,然后往上运动至右眼的特写,这只眼睛仿佛受了惊吓一般圆睁着;然后,镜头继续往前推进,仿佛进入眼睛内部的深度空间,在那里,像银河系一般的旋涡出现了。这种旋涡让人联想到了宇宙,在鲍威尔之前的一部作品《平步青云》(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1946)的开场,出现过银河系,而在该片的高潮处,我们也在大卫·尼文(David Niven)闭合的眼睑后发现了浩瀚的天堂。
希区柯克并不是不知道这部电影;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在筹备这部作品时,去过好莱坞,而招待他们的正是希区柯克,更有甚者,希区柯克解决了他们的选角难题,他提议让金·亨特(Kim Hunter)来演该片中美国电台接线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