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么,它在现代医学中境况如何呢?
现代医学的崛起,其核心是临床治疗的昌盛,这得益于人类认识和征服传染病的第二条线
路
——微观认识和个体治疗的进步。
医学在微观层面认识的深入,首先得益于早前出现的显微镜(17世纪末),发现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东西。1861年巴斯德发现发酵是外源性的微小生物引起的;1876年德国人科赫首次证明“细菌和疾病的关系”——炭疽杆菌就是炭疽病的病因。
其次,还有医学仪器的发展。最早的医学仪器算是温度计了,比如量一下体温,一看发烧了,就可以赶紧去看医生。现在的仪器很庞大,不能背着仪器到病人家里,我们就把病人带到了医院,从此医院就成了医疗实践活动的中心。然而伴随着医院崛起的,是公共卫生的衰落。
现代医学的体系可谓“三足鼎立”:基础医学,研究生物医学原理,为未来铺路;临床医学,主要是诊断和治疗;公共卫生,注重预防和人群科研。
然而在今天,公共卫生这一“足”太短了,致使医学这个“鼎”站立不稳,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得非常明显。
现代医学是以科技武装的以西医为主导的医学体系,基础医学是研究的主力,临床是实践的主角。公共卫生有什么用?如果不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公共卫生的存在,更不用说它是干什么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公共卫生从昌盛到衰微,从“巨人”变成了“矮子”。
科技使人类进入了物质文明最傲骄的时代。
科技的巨大成功使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血液里,使我们更相信新奇的东西,轻视古老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往往认为,“新奇的”就是最好的、最有用的,而传统的可能是迷信的、无用的。卫生是100多年前最先进的科技,用在控制今天的新冠肺炎一点都没有过时,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很难会相信它。
“分割”是科技另一个重
要特征。
我们各专业的人员多是专才,不是通才,很难把握全局,很难为整体决策拍板。另外,知识和科技作为巨大的生产力,也可以成为巨大的赚钱工具,利益经常会扭曲真理,经常使得我们对
信息真假难辨,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情况下决策的困难。
这是当下、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的大背景。
科技主导的现代文化决定了我们控制这场疫情的总体思路。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 (Bruce Aylward)在疫情之初的担忧表达了多数人的想法:“在应对这场瘟疫的准备和计划中,我犯了和很多人同样的错误,带着很多人同样的偏见,认为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我们怎么能控制住这场世纪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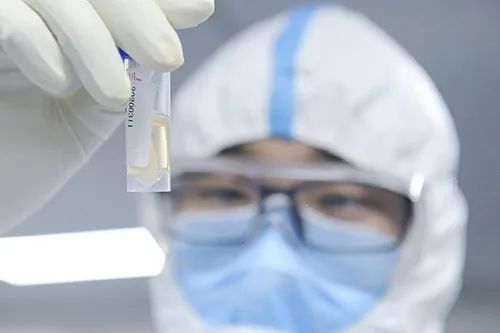
2020年3月12日,合肥,核酸检测人员在检视咽拭子核酸采样管。
由此控制疫情的思路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传染病,我们应尽快地分离出病原体,研制出诊断试剂,进而快速研发出疫苗和药物,希望以此最终能控制住疫情。我们的基础研究不负众望,在还没说清楚是否人传人之前,就已经分离出了病毒并研制出了病毒核酸诊断试剂。
然而,控制这场疫情真正依靠的是像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这些常识性的卫生措施,而不是最新科技。新科技也很重要,但只是辅佐,不是主药。
时至今天,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还在路上。
下一次疫情还将是如此,控制一个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不能坐等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科学必然不断进步,但传统智慧未必过时,这是这次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而且,科学和事实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值。
面对同样的疾病、同样的科技、同样的证据,世界各国采取的策略大相径庭,说明影响抉择的不完全是科技,还有科技之外的重要考量,那就是决策者对公众健康和生命价值的考量。
就像农业的问题不可能用医学来解决,同理,既然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灾难,那么战胜它的就必然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巨大胜利。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通过社会动员和组织,采取以隔离为主的卫生措施,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
这一切都是对公共卫生使命、理论和方法最好的注解,对公共卫生实践的一次最好的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