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记者:
靠链路这种电子数据传输的方式来控制无人机,就存在一个延迟问题,怎么能保证精确性和预知判断?
李浩:
一个动作要柔和,第二个量要适当,第三个注意力要分配。有人机一拉杆,飞机状态就变了,我们现在一拉杆它可能不变,接着第二次再操作,就有可能产生叠加量,引起飞机的震荡。
记者:
所以跟过去的习惯完全不同?
李浩:
不一样。另外还要有情景想象意识,飞到哪一点,什么样的动作,实景什么样,都要想象我在飞机上。
李浩今年54岁,在飞无人机之前,他是一名有着30年飞行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18岁时,经过招飞,李浩加入人民空军,几年后,他从航空大学毕业,分配到航空兵部队,先后飞过歼-5、歼-6、歼-7、歼-8等6种机型。

战斗机飞行员要在48岁时停飞。
2010年,
身为空军“王牌师”空一师的飞行尖子,李浩安全飞行3000多小时,即将达到战斗机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年限。表面上看,李浩日后的生活和其他老飞行员没什么不同,但停飞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他却迟迟没有动作,已经有民航公司为他开出了每月数万元的薪水,李浩仍然举棋不定。
李浩:
我性格比较倔强,飞行这个事业干了一辈子,从18岁开始接触,好多战友都被淘汰了,甚至还有好多牺牲的。我每一关都过来,一直飞到最后,这种感情特别难以割舍。有人机飞到最后了,我就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
记者:
那时候也有一些犹豫和彷徨?
李浩:
是的。当时我还跟领导说,和飞行工作相关的,包括航空调度都行。我还想在部队继续留下干,等干到55岁再退休。没想到这时,空军招收第一批无人机飞行员,所以当时我就赶紧报名了。
当时,美国、以色列等国的无人机,已在多场局部战争和任务中大展身手,展示出高度的成熟可靠性,并在作战理论和样式上取得突破。形势逼迫着中国的无人机训练也必须尽快起步,我国的无人机部队组建初期,一切都处在不确定中,李浩跟着部队转战大江南北,驻地和归属更是几经调整,
最终来到了西北的大漠深处。
从有人机到无人机,一字之差,
随之而来的却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知识结构的重塑。转型关键在于换脑,从空中转到地面、从座舱转到方舱、从舵杆转到键盘,一道道无形的坎儿,摆在李浩面前,挑战着这位年近五旬的老飞行员的极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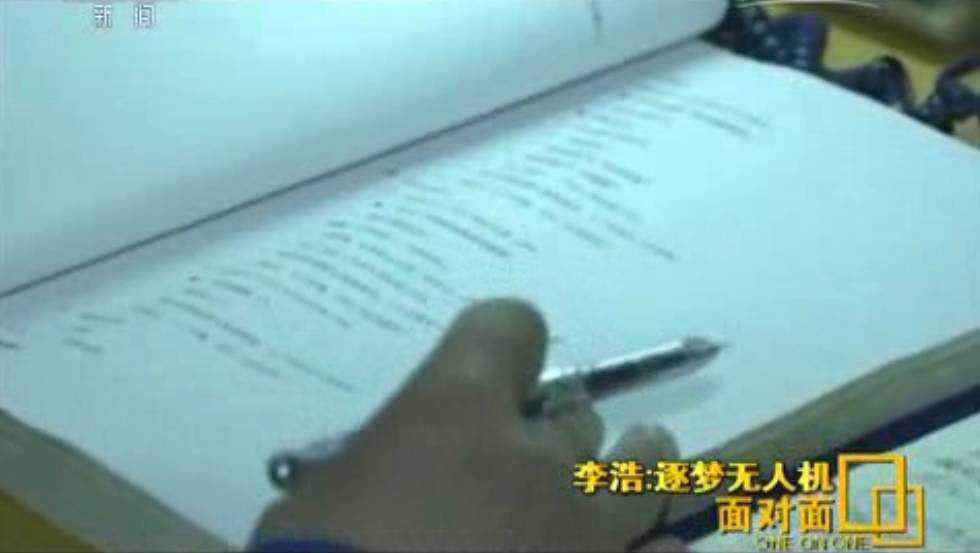
而且,与有人机不同的是,无人机是系统作战,需要飞行操控、任务载荷等多席位数人协同配合。要想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必须全面掌握多个领域十几门专业知识、工作原理,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当时年近五十的李浩,还是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理论课的学习,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军用无人机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