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贝森特
最棒的一点是,我们几乎什么都做。
我们进行研究、管理投资组合,团队中有两个人负责交易,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期权交易部。我当时在周末专门去上期权定价理论的课程,并开始涉足期权和期货交易。这让我意识到,投资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
奥莱因家族的投资风格高度集中,他们非常注重与管理层的关系,他们至今仍是伟大的长期投资者。
但我们可以通过杠杆和期权提高回报率,这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视角去理解不同的投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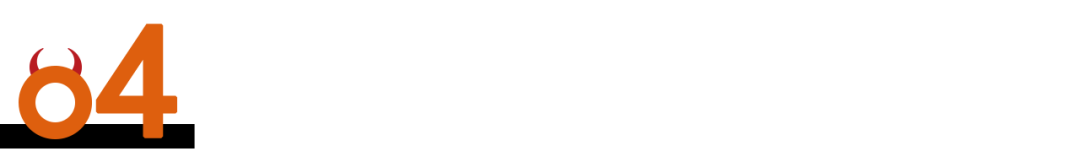
塞迪斯
你为什么决定在
80
年代中后期离开呢?
贝森特
当时华尔街有一种
“
管理层早餐会
”
的传统,高盛或摩根士丹利会邀请某家公司管理层举办早餐会。我在这些年里结识了吉姆
·
查诺斯,他是著名的做空投资者。
我们并没有在耶鲁大学重叠过,就像我和吉姆
·
罗杰斯一样,我们是通过
“
耶鲁校友
”
这个纽带认识的。
但我发现,我们在投资问题上的思考方式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吉姆
·
查诺斯是个悲观主义者,而
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
这让我回想起吉姆
·
罗杰斯的研究风格:深度研究,并验证故事的真实性。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做空策略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资产管理类别,而吉姆
·
查诺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
“
白鞋品牌
”
(原指代表常春藤文化传统的高端机构,现泛指在专业领域中历史悠久、声誉卓著、风格稳健的精英机构或人物)
。
当时,大多数做空者的形象都很神秘,甚至有些像影子交易员,他们往往通过散播故事来影响市场,整个行业名声并不好。
我认为,吉姆
·
查诺斯完全可以改变这一现状,并打造一个更专业、更透明的做空投资机构。
而我正是他的第一位分析师,也是公司的第三名员工。
塞迪斯
你是哪一年加入他的?
贝森特
就在
1987
年股灾之后,我是在
1988
年
9
月加入的。
塞迪斯
那时候做空市场是怎样的?
贝森特
当时的市场机会很多,分化程度更高。那时还没有一篮子交易,市场的指数成分股也不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但在美国证交会加强对欺诈行为的监管之前,市场确实更有刺激性。
那是一个目标丰富的市场环境,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比如里根税改、德州石油行业的崩溃。
此外,迈克尔
·
米尔肯(
Mike Milken
)和整个德崇体系(
Drexel Burnham Lambert
)正在引领一轮杠杆收购驱动的资产升值周期。那是一个适合精选个股的时代。
(
聪投注:
德崇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具创新性、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投资银行之一, 主要业务围绕垃圾债券市场,由迈克尔
·
米尔肯主导,使垃圾债券成为主流融资工具。
1990
年因内幕交易丑闻破产。)
我在
1988
年加入吉姆的公司,随后,德崇支持的联合航空收购案失败,我们在一个月内赚了
10%
。
接着,美国储贷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
1989
年和
1990
年是做空金融股的黄金时期,因为这一轮金融工程正逐渐走向崩溃。
塞迪斯
那个时代的金融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贝森特
这标志着通过储贷机构(
S&L
)进行的金融运作走到了尽头,德崇投行倒闭,而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德崇倒闭后,市场的混乱达到了顶点。而就在这场风暴的最后一幕,萨达姆
·
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市场进一步震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花旗银行的股价可能从
32
美元跌到了
4
美元。
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市场在遭遇一次极端情况时,往往会出现同样极端、但方向相反的错误反应。
例如,
1989-1990
年,储贷行业崩溃,需要政府出手救助。然而,美国货币监理署(
OCC
)的负责人克拉克(
Clark
)在
1990
年却恐慌性地执行了监管收紧,要求银行即使借款人仍在按时还款,也必须将某些空置率极高的房产按零价值计提损失。
这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
“
糟糕的政策
”
往往能创造出很好的投资机会。
塞迪斯
在你加入吉姆团队的时候,市场仍然经历着痛苦调整,随后才迎来转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如何衡量投资的价值?
贝森特
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否持有一只最终归零的股票。当时有太多这样的机会,很多公司最终真的归零了。
以
1990
年为例,标普
500
指数可能下跌了
18%-20%
,但我们的基金收益却高达
50%
。我们所做的投资基本上涉及三个层次:
市场贝塔,即市场整体趋势;
行业趋势,即特定行业的机会;
个股回报,我们捕捉到了许多最终归零的股票。
塞迪斯
从
1992-1993
年起,市场进入了大牛市。作为一名专注于做空的投资者,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的?
贝森特
哦,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在
1991
年就离开了(笑)。
塞迪斯
那可真是精准的市场时机(笑)。当时你的业绩很好,是什么促使你决定离开?
贝森特
我记得是在
1991
年
1
月,萨达姆
·
侯赛因最终入侵科威特。市场随即大幅反弹,许多资产变得极度便宜。
与此同时,我们的基金管理规模也增长迅猛。当市场下跌时,投资者涌入做空策略。
我刚加入吉姆团队时,我们的管理规模大概只有
3700
万美元,其中
1300
万美元来自合伙人基金;
2500
万美元来自索罗斯基金的托管账户。
但等到我离开时,规模已经增长到了
5
亿美元!
然而当市场开始回暖,我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做空标的。
有一天,我走进吉姆的办公室,说:
“
吉姆,我找不到任何值得做空的东西。
”
他回答:
“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
于是我说:
“
那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点别的。
”
塞迪斯
那你后来呢?
贝森特
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里办公。
我和索罗斯的团队关系很好,于是斯坦
·
德鲁肯米勒在
1992
年邀请我加入索罗斯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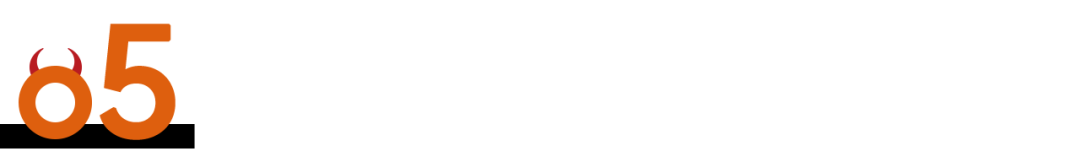
塞迪斯
索罗斯基金一直以全球宏观投资闻名。你如何定义这个概念?
贝森特
先回顾一下索罗斯及斯坦利
·
德鲁肯米勒的传统,所有人最初都是个股投资者。
乔治
·
索罗斯最初就是一名股票投资者,他在阿诺德
·
布莱
·
施罗德公司(
Arnold Bli Schroeder
)工作时,投资方法就是列出
10
只股票,然后与客户讨论这些股票。
斯坦
·
德鲁肯米勒同样如此,他也是从个股研究起步的。
但不同的是,索罗斯最终发展出了反身性理论,并将市场动态的宏观层面纳入投资框架。这就是
“
全球宏观投资
”
的雏形。
如果有人说服索罗斯某个投资是个坏主意,他会立刻撤掉,然后换上新的标的。
后来,他逐步扩展到宏观投资。斯坦利
·
德鲁肯米勒也是一样的路径。
斯坦利当年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匹兹堡
PNC
银行的研究部主管。他的投资思路有点类似我在布朗兄弟哈里曼的资产配置经验,直接扔掉传统的资产配置矩阵,在
70
年代把
40%
的资金投进石油股。
斯坦利最初也是个股投资者,但我认为宏观投资渗透在一切之中。
我的风格仍然受到杜肯(
Duquesne Capital
)的影响,即微观驱动宏观。我们可以从企业传递的信息中获取大量洞见。
例如:我们在
PCE
平减指数(
PCE Deflator
)上做不到比别人预测更准,也没办法建立一个比领先经济指标(
LEI
)更好的模型。
但如果卡车运输公司告诉你,业务正在起飞,那就很值得关注;
如果家得宝表示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那说明需求旺盛;
如果银行
CEO
透露信用卡坏账率正在上升,那可能是经济问题的前兆。
因此,股票投资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工具来实施投资策略。
塞迪斯
索罗斯和斯坦利在管理资金时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找到投资回报最大的机会的?
贝森特
他们会从多种角度权衡投资方法。
比如,如果认为油价会上涨,那么当钻井公司股票被大幅低估时,那就买入能源股;如果期货曲线显示未来三年油价会下降,那可能意味着可以通过期货曲线来进行对冲交易。
他们关注的核心是:在整个投资组合的背景下,如何思考这些机会?
塞迪斯
当有人推荐一个澳大利亚的投资机会时,风险团队可能一看数据发现,这东西和标普
500
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
R²
高达
98%
)。那你就得问了,这笔投资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好处?
”
贝森特
我们会关注一个核心问题:投资置信度有多高?
迈克
·
波伊安(
Mike Boian
)曾说,投资决策的关键是信心水平要超过
50%
的中位数。当你对某个投资越来越有信心时,就可以逐步加大仓位。
乔治
·
索罗斯有一句著名的话:
“
我只需要足够的信息来做决定。
”
他不是那种因为过度分析而错失机会的人。
塞迪斯
那么,如何在分散投资、集中投资和高信念投资之间找到平衡?
贝森特
如果你想持有高信念投资,并愿意集中持仓,那有时你可能会没有太多持仓,甚至得持有大量现金。
这在个股投资者中很常见,比如塞思
·
卡拉曼(
Seth Klarman
)就曾长期持有大量现金。你还记得我们当时一起读的《泰德
·
威廉姆斯的击球理论》(
Ted Williams’ book on hitting
)吗?
泰德
·
威廉姆斯被誉为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体育画报》(
Sports Illustrated















